2019年10月29日下午,由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所、宣传部及中华文化研究院主办的跨文化系列讲座第103讲在教四楼213会议室举行。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旅日学者张明杰老师带来了一场主题为“大村西崖与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的讲座,主持人是周阅教授。

一、为何讲大村西崖?
讲座伊始,张明杰教授向在场师生说明他选择大村西崖作为研究和讲述对象的原因——大村西崖是中日美术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何以重要呢?鉴于日本文化及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等因素,直至明治末期,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藏界一直偏重“古渡”作品,即旧时流入日本的南宗院体画(如梁楷、马远之作)和宋元时代禅宗画(如牧溪、玉涧之作)等,而极少接触到主流文人画作(如元四家之作),导致日本人对中国美术的鉴藏模式较片面、偏颇。开始改变这一状况的是以内藤湖南、泷精一、大村西崖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张教授认为,其中大村西崖贡献尤大。他著书立说、访华交流、创设机构、复制精品、编刊图录等,不仅将大量中国的书画精品介绍到日本,而且促进了中日书画艺术的交流,其中国绘画史相关著述对我国早期美术教育及教科书的编纂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二、大村西崖其人其事
张明杰教授以大村西崖的《自叙传》为主,介绍了其生平及研究业绩,西崖在少年时期较全面地接受了和、汉、洋学的教育。他既有“新学”(西学)知识,通晓西方美术及美学理论;又有汉学功底,汉诗文俱佳;业余又嗜好书画、佛教及佛教典籍。西崖是东京美术学校雕刻科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京都美术工艺学校任教,因而遍览关西古刹里保存的雕像、佛画,并把正仓院的宝物调查得一清二楚。西崖曾习文人画,称自己“稍得解翰墨之趣”,张老师随即向在场师生展示了西崖的书画作品,书法如锥画沙,绘画皴点有致,可见其造诣之深。
在京都任教两年后,西崖自觉“苟欲以学艺成家,则不居于帝都不可也。”便重返东京的母校任教,潜心于密教典籍的研究。但西崖对当时日本美术潮流持不同认识,尤其与校长冈仓天心“意气不相投”,遂于1897年辞职。翌年春,西崖为新校长所聘,重返东京美术学校,讲授美术史、神话等,创制了雕刻学科的教学体系,还与森鸥外共同编刊《审美纲领》等。之后西崖参加了万国博览会,还于欧美诸国巡览过西方雕刻及神佛图像,与所携希腊、罗马诸神传稿参照对比,以资研究。张教授强调,西崖此举乃近代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即重视史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我们往往忽略了实地考察,陈寅恪先生总结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仅以史料、出土文物为主。另外,张教授从西崖的研究方法还总结出:“做研究要从自身研究领域或课题的源头做起,看似不怎么相关,但实为其最根本之处。”

张老师继而介绍自1905年始大村西崖专事研究的成果。西崖以讲义为基础于1906年出版了《东洋美术小史》,是早期较系统完备的以中日两国为主的美术史。同时,与田岛志一等创设审美书院,刊行了大量精美高质的中日美术图籍,对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赏和普及做出了贡献。张老师除通过图片展示西崖参与出版的美术图籍之外,还简要介绍了西崖编撰的主要著作,如《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支那绘画小史》《密教发达志》等,对其来历和具体内容等可谓信手拈来,要达到这层纯熟境界离不开多年的精研史料和实地调研。
辛亥革命后,皇室、王府及高官所藏书画开始流出,其中部分流入日本。同时,通过大村西崖等人和出版机构的努力,大量过去从未寓目的书画得以眼见,日本人对中国美术的认识发生改观。但主流绘画精品依然不足,制约了人们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整体认识,尤其是对文人画的认识仍不够公正。日本人的文人画在菲诺罗萨等人的贬低之下,更是评价不佳。张老师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西崖极力倡导文人画之复兴,并于1919年跟同道筹划创设了又玄画社,积极从事文人画创作,每年定期举办画展,同时通过四处游历、游说以及撰写《文人画之复兴》、编刊《文人画选》等,以振兴文人画。

张老师指出,大村西崖访华前,其学术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已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对美术学界来说,西崖之名业已有一定知名度。西崖“怀抱欲游禹域之志久矣”,终于在1921年秋实现了访华的愿望。
三、大村西崖首次访华
西崖一生中曾五次来华,本次讲座中,张老师着重介绍其首次访华的经历。张老师指出,西崖首次来华的目的是观赏中国古代书画,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等。当时来中国游历数月需要一大笔资金,西崖向启明会申请援助遭拒,只好绘制了20双金屏风和书画,售得万余元作路费。同时,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也予以协助,并希望日本驻华使领馆对其提供帮助。张老师向在场师生展示了西崖的记述,他得见内府所藏书画并拍照留存,又购两百多种古书,还观看了日华绘画展览会,游览古迹,后由京、津前往沪、杭。张老师据西崖日记,详细考察了西崖的访华经历,具体到当天做了什么事、会见了哪些人,细致程度令人叹服。
其中,张老师着重讲了西崖与陈师曾的交往。他们经历颇相似,对文人画有共同的认识。陈师曾向西崖引见了诸多收藏家和画家,齐白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齐白石在北京寂寂无名,自陈师曾极力向西崖推荐后,他也逐渐得到公认。西崖将本次访华接触过的现代画家的作品和自传带回日本,出版了《禹域今画录》。西崖和陈师曾还谈论了《文人画复兴论》的中译及合著中国绘画史的事宜。张老师点出,我们可以从日记里看出在中日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一书的成立及出版过程。

但另一方面,完颜景贤以及蒋孟蘋等大藏家所藏名画的日本流入,也跟大村西崖的斡旋有关。如蒋孟蘋由于经商失败而欲出售其藏品的消息,大村西崖从金城处及早得知后,旋即告知大阪纺织界富豪阿部房次郎,使其购得部分书画藏品。在今天看来,大量古书画被卖到日本着实令人扼腕,但从当时流通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因为国内收藏家无法给出更高的价格。
张老师指出,西崖此行会晤了各地主要的收藏家,一览其藏品并拍摄带回日本七百余枚名画照片,后于东京、大阪等地讲演时展出,还将部分历代名画代表作编入《文人画选》和《中国名画集》。现今许多书画文物散佚,因而这些照片十分珍贵。

张老师随后总结了西崖首次访华的六大收获:一是赏画并拍照、购书籍,不仅有助于个人和学界的研究,而且丰富了日本的中国书画鉴藏;二是在中国美术界初步建立了可互动交流的人脉关系网络;三是积极联络中国现代画家并将其作品介绍到日本;四是通过与陈师曾的交流和往来,促成了作为近代中日美术史上一大历史性文献——文人画论著的诞生;五是此次访华促成西崖一大构想及其实现,即以“图本丛刊”形式刊行中国古版画图谱珍籍。六是计划在华设立“日本翰墨俱乐部”,即后来在杭州西湖畔诞生的中日画家俱乐部(西湖有美书画社)。可以说,前三项是西崖当初的目的,均圆满实现,而后三项则是意外收获,在近代中日美术交流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张老师通过《萝轩变古笺谱》原书,以及《集雅斋画谱》《顾氏历代名公画谱》《萧尺木离骚图》《烈女传》等书影,就西崖刊行的“图本丛刊”做了重点讲解,对西崖为保存精美木刻雕版文献,弘扬版画艺术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西崖是真正的中国古版画的海外知音。此外,还简要介绍了大村西崖所摄李公麟《五马图》和董源《寒林重汀图》的递藏情况,以及其后四次访华的主要事项。
最后,张老师总结道,大村西崖在中日美术交流史上留下了鲜明的足迹,尤其是在当时西学流行、官制美术主导的近代日本,他能以较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美术尤其是书画作品,同时积极投身于中日书画交流活动,与中国的书画家、收藏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将我国现代画家及其作品介绍到日本。从旨在去中国化的近代日本官制美术史来看,大村西崖可谓独特的存在,虽然他早逝,但他在中日美术交流史的地位应得到充分肯定。
张明杰教授的演讲结束后,讲座进入了交流互动环节。

主持人周阅教授总结道,张教授今天为我们呈现的只是他头脑里的冰山一角,张老师是“行走的资料库”,是跨界的学术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秦刚教授分享了一段史料:芥川龙之介和西崖曾看过宫中借出的字画,与后来书画流失也许存在联系,对这些事项的考证极具文化史价值。北京社科院的陈言研究员提出了“南宗画、禅画传入日本并形塑其审美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的问题。张教授认为更接近必然,因为受其历史和审美等因素影响,早期来华的大都是留学僧,带回的多是佛像和禅宗画。而日本人热衷的茶道,尤其是狭小而又阴暗的茶室也给其鉴藏中国绘画带来了一定制约,如一些宋元画卷进入日本后甚至被裁成小幅使用。北京社科院的张泉研究员则认为更接近偶然,因为任何一个学科处于早期时都无法全面了解情况,如西方汉学早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就是“碰到什么抓什么”。
张明杰教授考据严谨,将对象放在历史语境中研究,以大村西崖这一人物线索“顺藤摸瓜”,连结起中日美术交流史。众师生都盛赞其重视史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除了上述几位老师外,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魏崇新教授、中国社科院的范智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妍教授、三联书店大众分社主任叶彤编审、北京语言大学的陈戎女教授和众多中外学生一同聆听了此次讲座。本场讲座在精彩的互动和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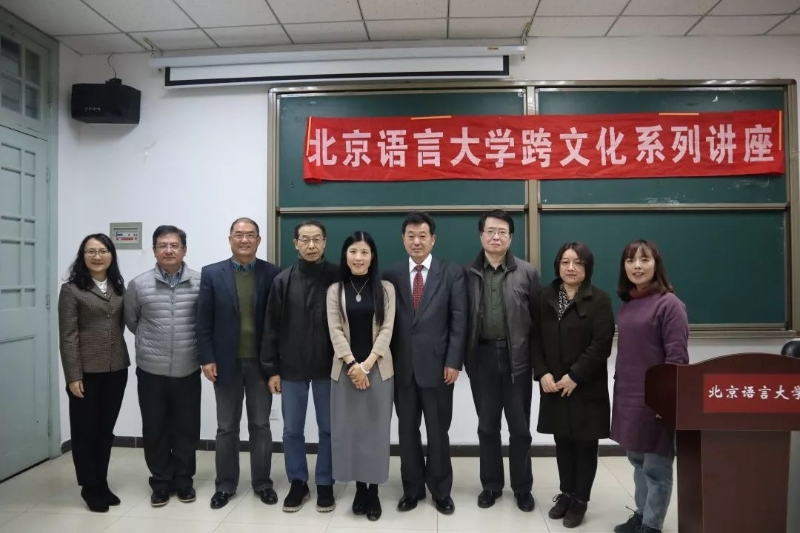
注释:
[1]为保留历史原貌,本文对书名中出现的“支那”字样不做改动。

